金克木:1 912年8月14日—2000年8月5日,中国着名文学家,翻译家,梵学研究、 印度文化研究家,与季羡林、 陈玉龙并称“北大三支笔”,和季羡林、 张中行、 邓广铭一起被称为“未名四老”。
01/诗的倒读
电子计算机流行,程序概念普及了。程序中有个次序问题。次序不仅是时间排列,更在于意义和作用的变化。下棋和打桥牌中先后次序重要,语言也是这样。旧诗有集句、摘句和回文体,历来作为文字游戏,其中含有诗的特性。
顺读和倒读,有的诗不行,有的诗可以由此发生变化。“王师北定中原日,家祭勿忘告乃翁。”倒为:“家祭勿忘告乃翁:王师北定中原日。”前者只是嘱咐,后者就含有对日期的信和疑的两面了。“落红不是无情物,化作春泥更护花。”倒为:“化作春泥更护花,落红不是无情物。”前者先判断后证明,后者先见现象后出解说。若不拘词律,“春花秋月何时了?往事知多少!小楼昨夜又东风,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。”可倒为:“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。小楼昨夜又东风!往事知多少?春花秋月何时了!”诗意同而韵味异。诗句顺倒,标点不同。小说《黑骏马》中的民歌也可以顺读或倒读。可以从“漂亮善跑的——我的黑骏马哟”开始,也可以倒过来,从“那熟识的绰约身影啊,却不是她”开始。原无标点,更易颠倒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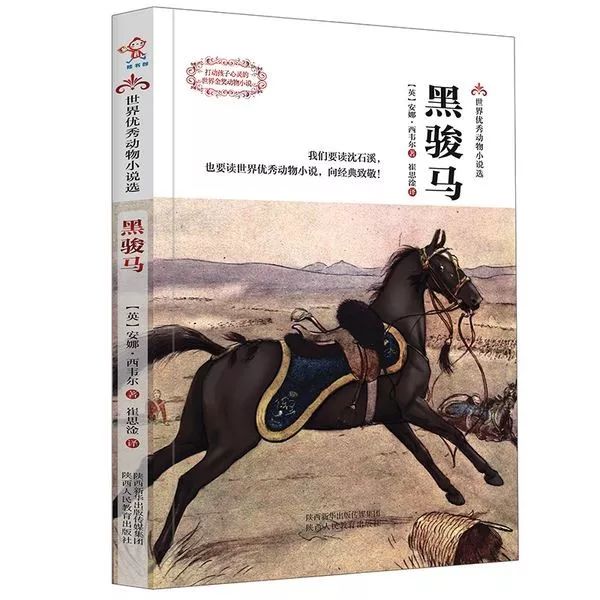
当代不少新诗被认为难懂,读者不妨自己重新编排一下试试。何不把人家的诗变成自己的诗?这不是游戏。这里有窍门(外国诗另案办理)。
02/ 书的反读
读书有正解、误解和不解;可以正读,也可以反读。例如《资治通鉴》,本来是资“治”的,也可以读成资“乱”的。因为讲治就必须讲乱,无法避免。讲成功的王同时得讲失败的寇。书中讲的治世还不如乱世多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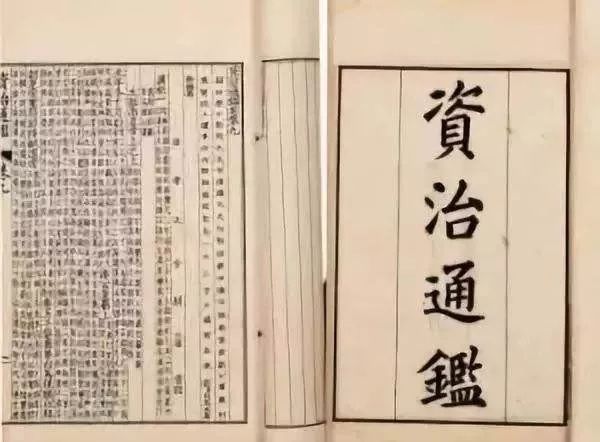
一开头,司马光长篇大论仿佛作总序。他说君臣的礼和名分最重要。微子和季札宁可亡国也不破坏“大节”。上有桀纣之暴而下有汤武之仁,就不能不亡国了。可见名分可以保国,也可以失国。要使天下大乱的最简单办法是使帝王昏聩,干坏事,倒行逆施。这样,名分的作用就到了反面。由赵高开始的捣乱传统就是这样。他又说:“君臣之礼坏矣,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。”反读之就是,以智力相雄长必然要破坏君臣名分。
又如《论语》中孔子说:“学而时习之,不亦说乎?”这话的答案可以是正的,也可以是反的。学习而不悦的人有的是。要看学什么,怎么学,是自己要学还是被逼迫而学。《春秋》第一句“元年春王正月”。《公羊传》和《谷梁传》提出许多问题和答案。这也可以反读,把“传”当作“经”,作为公羊高要讲“大一统”而引“王正月”作证。事、物、语言都各有正反两面。全是结论和定案的课本也有反面,问不得的。可是怎么能禁止人口头正读而心中反读呢?任何神圣经典都办不到。那就只好用严刑诛心了。古今中外莫不如此。
03/歧义语
语言都有歧义,即多种解说。汉语特别善于运用歧义语。《论语》中孔子所讲的“仁”,他自己就有许多不同解说。写错别字多半是只知音形而不知有歧义字,任意简化或繁化,假借出了格,以为都可通用。标点古书的困难不仅在于歧义词,还在于歧义语。
有时很难确定用逗号、分号或句号,特别是在不同断句都能讲通的地方。这也给翻译造成困难。俗话也有歧义。“世上无难事,只怕有心人。”好像“有心人”倒是“难事”了。常用语“生前”指的是“死前”。现代话也有。“陪斗”是“助拳”斗别人呢,还是陪人挨斗?十年前谁都明白,将来只怕需要考证了。“男人的一半是女人”,是指“半男半女阴阳人”呢,还是指男人中有一半变成女人了?
不仅文学作品中大量存在,哲学,史学,甚至科学以至一般语言中也少不了。“走向世界”并不是说出发点在世界以外。“东方”指从中国向南、向西一直到非洲,却往往不算东邻日本,也不算中国自己。这些有没有自身的规律?为什么语言中不能没有歧义语?为什么大家都用?怎么用的?和思想有什么关系?许多问题需要解答。看是语言学,实是哲学。
04/ 如何给书“看相”?
现在人读书有个问题:书越来越多,到底该怎么读?
汉朝人东方朔吹嘘他“三冬,文史足用”。唐朝人杜甫自说“读书破万卷”。宋朝以后的人就不大敢吹大气了。因为印刷术普及,印书多,再加上手抄书,谁也不敢说书读全了。于是只好加以限制,分出“正经书”和“闲书”,“正经书”中又限制为经、史,甚至只有“九经、三史”要读,其他书可多可少了。
现在我们的读书负担更不得了。不但要读中国书,还要读外国书,还有杂志、报纸,即使请电子计算机代劳,我们只按终端电钮望望荧光屏,恐怕也不行。一本一本读也不行,不一本一本读也不行。总而言之是读不过来。光读基本书也不行:数量少了,质量高了,又难懂,读不快,而且只是打基础不行,还得盖楼房。怎么办?
也许理科的情况好些,不必再去读欧几里得、哥白尼、牛顿的原着了,都已经现代化进了新书里了;可是新书却多得惊人,只怕比文科的还生长得快。其实无论文理法工农医哪一行,读书都会觉得忙不过来吧?何况各学科的分解、交叉、渗透越来越不可捉摸,书也跟着生长。只管自己一个研究题目,其他书全不看,当然也可以,不过作为一个社会活动中的人若总是好像“套中人”,不无遗憾吧?
现在该怎么读书?假如必须说点什么,也许只好说,我觉得最好学会给书“看相”,最好还能兼有图书馆员和报馆编辑的本领。这当然都是说的老话,不是指现在的情况。我很佩服这三种人的本领,深感当初若能学到旧社会中这三种人的本领,读起书来可能效率高一点。其实这三样也只是一种本领,用古话说就是“望气术”。古人常说“夜观天象”,或者说望见什么地方有什么“剑气”,什么人有什么“才气”之类,虽说是迷信,但也有个道理,就是一望而见其整体,发现整体的特点。
用外国话说,也许可以算是一八九〇年奥国哲学家艾伦费尔斯(Ehrenfels)首先提出来,后来又为一些心理学家所接受并发展的“格式塔”(Gestalt完形)吧?二十世纪有不少哲学家和科学家探讨这个望其整体的问题,不过不是都用这个术语。从本世纪初到现在世纪末,各门学术,又是分析,又是综合,又是推理,又是实验,现在仿佛有点殊途同归,而且越来越科学化、数学化、哲学化了。这和技术发展是同步前进的。说不定到二十一世纪会像十九世纪那样出现新局面,使人类的眼光更远大而深刻,从而恢复自信,减少文化自杀和自寻毁灭。
从前“看相”的人常说人有一种“格局”。这和看“风水”类似。王充《论衡》有《骨相》篇,可见很古就有。这些迷信说法和人类学、地理学正像炼丹术和化学,占星术和天文学一样,有巫术和科学的根本区别,却又不是毫无联系,一无是处。不论是人还是地,确实有一种“格局”(王充说的“骨法”),或说是结构、模式,不过从前人由此猜测吉凶祸福是方向错了,结论不对。但不必因此否认人和物自有“格局”。

从前在图书馆工作的人没有电子计算机等工具。甚至书目还是书本式,没有变成一张张分立的卡片。书是放在架上,一眼望去可以看见很多书。因此不大不小的图书馆中的人能像藏书家那样会“望气”,一见纸墨、版型、字体便知版本新旧。不但能望出书的形式,还能望出书的性质,一直能望到书的价值高低。这在从前是熟能生巧之故。
从前的编辑“管得宽”,又要抢时间,要和别的报纸竞争,所以到夜半,发稿截止时间将到而大量新闻稿件正在蜂拥而来之时,真是紧张万分。必须迅速判断而且要胸有全局。许多人由此练出了所谓“新闻眼”、“新闻嗅觉”、“编辑头脑”。以上说的都是旧社会的事。“看相”早已消灭了,图书馆和报馆也不是手工业式了,人的能力很多都让给机器了。
可是读书多半还是手工业式,集体朗诵也得各人自己听,自己领会,所以上面说的“望气”本领至少现在对于读书大概还有点用处。若能“望气”而知书的“格局”,会看书的“相”,又能见书即知在哪一类中、哪一架格上,还具有一望而能迅速判断其“新闻价值”的能力,那就可以有“略览群书”的本领,因而也就可以“博览群书”,不必一字一句读下去,看到后头忘了前头,看完了对全书茫然不知要点,那样花费时间了。
据说诸葛亮读书是“但观大略”,不知是不是这样。这也不见得稀奇;注意比较,注意“格局”,就可能做到。当然搜集资料、钻研经典、应付考试都不能这样。
其实以上说的这种“格式塔”知觉在婴儿时期就开始了。辨别妈妈和爸爸的不同不是靠分析、综合、推理而来,也不是单纯条件反射。人人都有这种本领,不过很少人注意自己去锻炼并发展。科学家对此的解说还远未完成,所以好像有点神秘,实际上平常得很。
先练习看目录、作提要当然可以,另外还有个补救办法是把人代替书,在人多的地方练习观察人。这类机会可多了。书和人是大有相似之处的。学学给人作新式“看相”,比较比较,不是为当小说家、戏剧家,为的是学读书,把人当作书读。这对人无害,于己有益。“一法通,百法通”,有可能自己练出一种“格式塔”感来。也许这是“宏观”、“整体观”的本领,用来读书总是有益无害的吧?